【摘要】
1923 年《汕头市政之工务计划》的编制实施,使汕头城区进入了“有规划建设拓展” 阶段。《汕头市政之工务计划》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由中国人自主制定和主持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本文着重分析了这一计划编制及实现过程中的设计理念、经费筹募、政商关系、实施体制等,如何顺应汕头商贸网络、商品结构、商贸形态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
【正文】

图1 民国印花税,陈黉利栈银票,图片来自7788收藏网。
经费问题是城区改造计划能否实施的核心问题。汕头和当时国内其它城市的做法一样,除了政府例常的“征费”之外,主要还是依靠商绅居民自筹和政府的土地收入。
(一)行政当局和投资者都有意识地借助“级差地租”来拉动投资需求
1921年至1934年间汕头市新辟建的20多条宽敞的骑楼马路,取代内街成为新兴业态的商业场所,大大提升了城区土地和道路的商业价值,汕头市区的商贸、消费的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直接拉动了国内外工商机构、海外华侨和本地市民的投资需求。
1925年萧冠英在《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一书中,已经关注城区道路系统建设与土地“级差地租”变化之间的关系:
“近以地价腾贵之故,报酬中人之金,改为买卖主之双方各给百分之一(即一分)。表面虽无前此之多,实则获利更复为厚。汕头地价,年年增高,预料沿岸长堤竣工、马路筑成之后,地价腾高,较今为甚。”
书中记载,1920年汕头市区尚未大规模辟建马路时,位于“四永一升平”和“四安一镇邦”的商业中心区,每井(即每平方丈)的地价都在180-260元(汕币)左右,其中镇邦街和至安街的每井地价高达300元,“闹市”(“老开埠区”)的行街、顺昌街、银珠街只有100元,南岸线新填海地段的广州街、商业街才70元,福合沟以东、以北地段的地价仅在30-60元左右。追求更高的级差地租,成为这座新兴商业城市“绅民”们积极参与辟建马路,进行城区改造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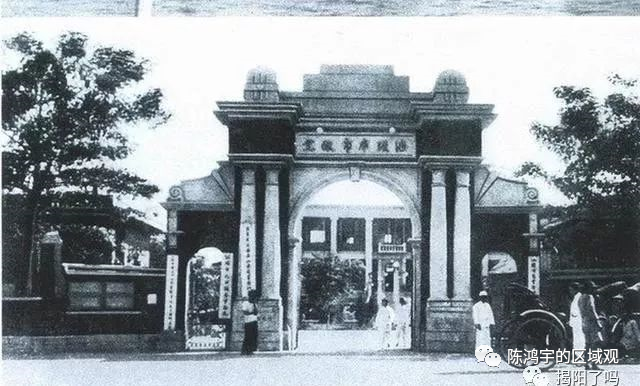
图2,城区东部市政厅周边新填海地块的地价,远低于西部组团核心商圈。
(二)汕头城区改造创造了旺盛的投资需求
汕头城区改造中,沿20多公里新建马路开建的数千栋楼房,为汕头市区创造了旺盛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需求。
表1 汕头开埠至1949年市区新增建成房屋面积
上表根据广东省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汕头市志》第三册,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卷五十三·房地产”的“第三章房屋建设”的数据计算。该章另称:开埠后至1949年,新建房屋面积2640879万平方米,年均增加29672平方米。其中住宅1814639平方米,占68.72%;非住宅825940平方米,占31.28%。
如表1所示,1949年汕头市区的房屋,75%以上是1905-1938年间所建,其中大部分的骑楼、住宅、别墅,都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城区“有规划改造”时期中建成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迅速扩张,使建筑建材贸易成为新的产业投资热点。
据潮海关统计,1919年汕头口岸进口水泥货值仅27014关两。按当年进口水泥每司马担1.020关平两换算,这一年汕头口岸仅进口了1589吨水泥。1927年汕头口岸进口水泥货值已经增加至126862关平两,1931年剧增至407651关平两,按当年进口水泥每司马担1.585关平两换算,进口水泥已达15431.58吨,为1919年的9.71倍,12年间水泥进口数量每年平均增长20.86%,其中1927-1931年4年间,每年平均增长33.89%。
1919年汕头口岸进口铁、生铁、钢类的货值仅为367880关平两,1928年增加至750995关平两,为1919年的2.04倍;1931年再增至974727关平两,为1919年的2.65倍。从1885-1915年的30年间,汕头口岸进口铁枝铁条数量大致保持在2万担左右到3万担之间。1920年和1925年进口数量分别为4.3万担和7.8万担,1930年达到10.64万担。
1935年刊行的《潮梅现象》称:“汕头为华南重镇,潮梅出入口门户,当前数年外汇高涨时,一般华侨纷纷汇款返国,投资购地,建筑楼屋,是以地价高涨。”“据建筑工厂中人言,汕头前数年,全市每年建筑价值达六七百万元,距近年来,因市情不景,逐渐低减。廿三年(1934年)全市建筑价值仅存五十万元左右。迨廿四年(1935年)建筑更形冷落,查全市建筑工厂大小不下二百家,现在营业均形寂寞。”尽管此时汕头城区的建筑业企业仅剩“不下二百家”,就企业个数而言,仍居于全市各行业首位。
(三)政府积极主动通过拍卖筑堤填海地和部分公地,筹措城区改造经费
《汕头市政之工务计划》中明确指出:“汕市最好之模范市场,全在现堤工计划、所填筑之海坦中,而市政之能否发达,亦概以此为命脉。盖自有此堤工,而后整顿市政之经费始有可希望。“
这份计划将‘筑堤所需之经费,及堤成后所得新地之价值”,编制了预算。预计填堤费用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一元,“所填成之新地基,共得七万四千零三十四井,除去堤岸及马路所占面积二万八千七百零九井外,实得面积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五井,每井估值银二百元,共可得银九百零六万五千元。”[6] 《1922-193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指出:这十年间政府的“堤工局”就开垦了38044000平方英尺的海滩地,政府可得其卖家的60%。亦即实际填地318096井,超过1923年计划的4倍多。如果按1923年地价计算,这十年堤工局卖地收入可得3600万元左右,如政府得其60%,亦有2000万元,远远高于1923年计划960万元的预算。
(四)多个因素叠加,促成了20世纪20-30年代潮籍华侨投资汕头城区房地产业的热潮
林金枝、庄为矶在1958-1960年对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调查所得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于1989年出版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书中将1862年至1949年华侨在广东投资分为初兴期(1862-1919年)、发展期(1919-1927年)、全盛期(1927-1937年)、低潮阶段(1937-1945年)、新高潮和崩溃阶段(1845-1949年),并对各阶段广东华侨投资各地区各行业情况进行了统计。根据书中数据,笔者整理了华侨投资汕头市房地产业的情况。
表2 1862-1949年华侨投资汕头市房地产业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如表2所示,1862年-1949年华侨投资汕头市的房地产业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投资房地产业的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42.63%,远高于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投资。
二是汕头城区房地产业的兴盛时期仅存在于1927年至1937年这10年间,这一期间华侨每年平均投资于房地产业的金额为146.6万元,高于“初兴期”的4.6万元、“发展期”的45.7万元、“低潮阶段”的22.56万元。虽然低于1945-1949年期间的214.4万元。但1938年-1949年全市新增建筑面积仅为37400平方米,仅占1949年以前城区建筑面积的1.45%。可见,1945-1949年新增的房地产投资,绝大部分并不是由于新建房屋,而是用于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原有建筑物。
三是1921年汕头城区开始“拆街建路”,南洋华侨随之扩大了房地产投资,但态度还是比较谨慎。1927年左右“西部街区组团”的近代道路系统基本成型,“东部组团”的城区框架已经拉开,重点地段的地价不断上升,城区房地产业的投资价值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才形成了华侨的房地产投资热潮。
四是华侨对房地产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建造或购买房屋,用于自住或出租。“据1959年汕头市房地产管理局提供的材料,当时汕头市房屋有4000多幢,其中华侨的产权约有2000多幢,占50%以上。”(1999《汕头市志》)1919-1937年间华侨在汕头房地产投资户数虽然不少,但单笔投资额偏小,平均每户投资仅在1万元左右。
关于这一时期华侨“乐于投资房地产”的原因,林金枝、庄为矶认为,一是20世纪20年代汕头市政当局实行市政改革;二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危机波及南洋各国,华侨返国日众”;三是农村不安宁,“只好停留汕头,另辟新居,或在汕头自谋生路”;四是在汕头城区投资房地产业的回报比投资其它行业可观。
如果将这一时期华侨回汕头购置和投资房地产业的行为放到近代潮汕经济的运行范式中分析,似可得到以下推论:
一是20世纪20-30年代,潮汕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态势继续深化,汕头城区已经逐步取代潮州成为韩江流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发展预期被普遍看好。1923年《汕头市政之改造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正是顺应了这一非均衡发展态势,创造了上述4个因素可以在汕头城区改造中发挥叠加作用的条件。
二是近代潮汕经济中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均与每一阶段的国际、国内市场间形成了“多维度循环关系”,华侨回到祖居地自建房屋或购置房产,是近代潮籍华侨实现顺畅的“代际循环更替”的重要链节,并不仅仅是是“叶落归根”的文化惯性使然。
三是经过几代潮籍华侨的艰辛努力,20世纪初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潮汕地区前往南洋地区谋生的居民,已经基本在南洋地区站稳脚跟,由开埠早期的“强迫劳工”身份(“被卖猪仔”和所谓“契约劳工”),已经逐渐转为“自愿”为改变生存处境而下南洋。越来越多的潮籍华侨获得自由迁徙权,促成“海外潮人社会”和“海外潮货市场”发育成型,20世纪20年代之后,不论汕头口岸出口的地方特色产品,还是和南洋华侨汇入汕头的侨汇,均出现快速增长,说明潮籍华侨已经有条件从南洋溢出资金、商品回哺潮汕。
四是这一时期汕头城区通过市政改造初步形成的近代商业城市雏形,相对于乡村地带更加优质的人居、交通、教育、医疗资源和公共治理环境,很自然地吸引着南洋华侨回馈的大笔资金,在汕头城区投资购置和建筑住房,就成为当时潮籍华侨较高质量、较低风险实现“代际更替”的首要选项。
来源:“陈鸿宇的区域观”微信公众号










